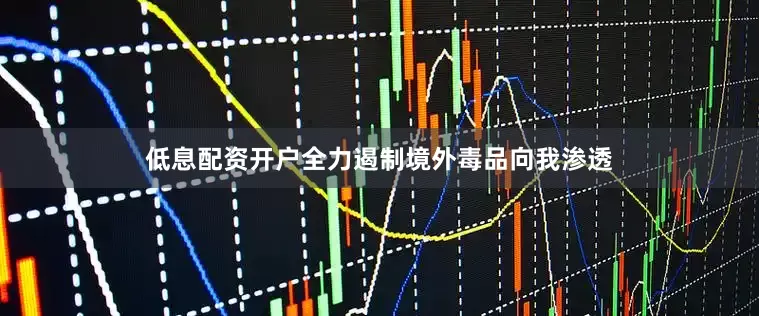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携手其他三个部门合力编撰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一文中明确提到:自1949年初至1952年2月,镇反运动历经两个阶段逐步推进。在此期间,总计镇压了超过157万6100名反革命分子,其中约87万3600人被判处极刑。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共立足未稳。从1950年开始,全国各地频繁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电厂和电话线被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从国民党军转变为土匪的武装势力,甚至频频纠集人马,进攻正在被共产党改造的县城。
1950年三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发布报告指出:近期,川、康、云、贵等西南省份频现土匪势力在当地煽动的规模庞大的武装叛乱事件。
报告进一步指出,尽管我国中央政权已然建立,但尚未全面掌控各地区统治权。自二月五日起,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爆发了一场近万名土匪参与的暴乱,致使我军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五十余名前来支援的干部战士英勇牺牲。虽然我军成功予以剿灭,但在此后的二月里,各地土匪势力再度猖獗,纷纷围攻并占领了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繁以及川东的秀山等多座县城。
解放初期的上海,反动势力猖獗至极。一方面,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产生的权力真空,导致了严峻的社会治安挑战;另一方面,众多散兵游勇与难民蜂拥而至,与原本就为数众多的底层流氓无产者相互勾结,趁机搅动局势,企图浑水摸鱼。
初步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解放上海的最初七个月里,各类犯罪活动呈现高发态势。强盗案件累计达到737起,盗窃案件更是高达11430起,抢劫案件则有530起。其中,1949年6月,即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盗案便激增至173起,日均发生约五六起;盗窃案件更是高达2205起,日均发生量超过七十起,情形尤为严峻。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渗透,意图颠覆中共政权。
毛泽东自苏联考察归来不久,正值身体调养期间。在共产党副主席刘少奇的领导下,1950年3月16日,党中央陆续颁布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剿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对象称“敌特党团”囊括了国民党军队成员、地方官员、特务、三青团成员以及会道门头目等各式人物。他们被视作破坏新政权建设的核心势力。警方与干部们随即展开深入调查,翻阅档案,并积极倡导民众踊跃举报,揭露这些不法分子。同时,敦促他们主动坦白身份,以便核实后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当时的北京市委报告显示,自解放军进驻京城至报告发布之日,本市已对逾6900名敌对特务、党团成员实施了逮捕、集训与登记。相较之下,南方的局势显得更为严峻。在山东,登记在册的土匪、恶霸地主、反动道会首领、特务以及反动党团骨干等五类人员,总数高达13万7599人。
浙江省的登记人数已超过11万。这些人被冠以一个全新的标签——“反革命分子”。刘少奇同志郑重指出,当地必须对这部分人群实施严厉打击。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分子”四个字,在共产党人眼中,便是最大的敌人。
与刘少奇和地方大员着急镇压反革命的态度不同,毛泽东不认为镇反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他虽然同意“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但他认为当前工作的重心是让财政与经济情况好转。
然而,在共产党内部,部分干部对现状表示忧虑,认为这不利于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在战火中失去至亲的家庭,对新生政权的信心遭受了侵蚀。同时,这也加剧了反革命势力对新生政权的攻击,使其变得更加频繁。
同年7月23日,政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该文件遂成为推动后续大规模镇反运动启动的核心依据。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短短三个月内,毛泽东的立场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
当时,蒋介石重返台北,重新开始履行职责,他将朝鲜战争视为国民党重振旗鼓的良机。那些忠实地追随蒋介石的大陆五类人士,也开始期待着能够动摇这红色政权的根基,哪怕只是局部或微小的波动。因此,加强镇压反革命行动显得尤为迫切。
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策,决定派遣军队前往朝鲜提供支援。紧接着,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了对反革命势力的镇压行动。
鉴于镇反运动起始阶段法律依据不足,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对“反革命罪”进行了明确界定,规定:“凡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策动、诱使或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组织或参与武装叛乱,加入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及公共设施,实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民众对抗政府或挑拨民众团结,制造及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或包庇反革命罪犯等行为,无论是否已付诸实施,均属‘反革命罪’。”此规定使得“反革命罪”的界定更为广泛,为刑罚的判定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自此,各地区的数字呈现连续上升的趋势。2月17日,北京市在短短一夜之间逮捕了675名反革命分子,次日便对其中58人进行了公开处决。3月7日的夜晚,北京再次一次性逮捕了1050人。紧接着,3月13日的夜晚,重庆市总计抓捕了4270人。到了4月10日的夜晚,南京的抓捕行动中逮捕了1200多人。而在4月27日的大规模逮捕中,上海抓获了8359人。
1951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

自六月一日起,全国范围内,无论杀人事件发生频率的高低,一律将捕人批准权限提升至地委和专署级别,杀人批准权限则提升至省级。各区域不得擅自更改此规定。”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浪潮历经一番势不可挡的洗礼,全国范围内的镇反工作逐步进入一个更为谨慎的收缩阶段。
自那时起,“镇反”活动演变为“三反”与“五反”运动的中心。“三反”运动聚焦于国家机关与企业内部,旨在推动“反贪污”、“反浪费”及“反官僚主义”的行动;而“五反”运动则直指私营企业,旨在抵制“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及“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
自1978年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对建国以来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中,诸如“镇反扩大化”等事件中的不实指控与冤假错案进行全面的平反。在这一过程中,大约三百万名党员干部的冤屈得到了昭雪,其中四十七万人重新恢复了党籍。
今宵,执行号角吹响:旨在肃清反动势力——独家对话前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要员况浩文
自重庆迎来解放的曙光,年仅19岁的况浩文便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初创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五处。该处肩负着边境保卫的重任,主要负责西藏与云南边界的安宁。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总部坐落于重庆,这座在战火中曾是国民政府陪都的城市,反动势力根深蒂固。也正因此,重庆成为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前线要地。
重庆的镇反运动历经三次规模较大的集中行动,其中,况浩文亲历了1951年3月13日那场举世瞩目的重大抓捕。该行动在重庆的镇反运动中尤为惨烈,规模宏大,被后世永远铭记为“三一三大批捕”。此后,况浩文凭借中篇小说《一双绣花鞋》名声大噪,而这部作品的灵感与故事背景,正是源于那次抓捕事件。

曾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一员干将,同时也是脍炙人口的小说《一只绣花鞋》的创作者,况浩文先生才华横溢,让人不胜敬佩。
首任市长车遇爆炸。
提问者发问:在即将展开的镇反行动中,重庆与其它区域有何显著差异?
况浩文(以下简称况):恰逢重庆宣告解放,我恰巧位于市中区的陕西路。自此,我投身于工作,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尽管回忆有所模糊,但对当时的方位记忆依旧清晰。11月29日,蒋介石及其子撤离重庆,飞往成都,意图与解放军进行最后的抗争。在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两次亲临重庆,部署所谓的“应变计划”。为执行此计划,国民党特务总队曾在重庆集结,他们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当时,人们常用“敌情严重,社情复杂”来形容局势的紧张。
记者提问:在重庆地域内,哪些人被判定为反革命分子?目前,原国民党在重庆及其西南区域的影响力现状是怎样的?
在我军方面,宋希濂指挥的军团在川东北地区遭到了我军沉重的打击。蒋介石随即紧急派遣其精锐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从陕西紧急增援,意图与解放军展开决战。两军于重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战后,敌方主力多数溃散逃往成都。只有少数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有的选择了起义,有的则随国民党政府撤退。重庆市长杨森便是其中跟随蒋介石撤退的一员。随着部队的溃败,部分士兵加入了匪帮,而另有部分士兵则潜藏于乡间,伺机行动。
在警方领域,国民政府内政部的第二警察总队仍有一部分成员留守于重庆。这些成员原本是经过改编的正规师团,拥有相当可观的战斗力。至于宪兵体系,先前宪兵司令部及其下辖的宪兵团,也汇聚了众多人员。此外,各类特务的身影亦随处可见。重庆的特务种类繁多,无所不包。其中涵盖军统、中统、四川特委会成员,以及众多非正规特务,我们统一将他们称为“杂特”。
概而言之,涉及的对象涵盖了军队、警察、宪兵、特务,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党团核心成员,甚至包括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随着国民党撤离重庆,他们在白公馆内枪杀了共产党员,却对众多重罪刑事犯予以释放,其中不乏原本应受死刑者。此类人数颇为众多。鉴于各地陆续解放,重庆成为最后一个解放的城市,因此大批特务从各地逃至重庆。当时重庆的人口不过百余万,然而这些社会渣滓和反动势力却多达上万人。这一现象突显了我们开展镇反工作的紧迫性,“敌情严峻,社情复杂。”
往昔,蒋介石曾力图将国民政府迁回广州二次。然而,终在解放军的炮声隆隆中,他们不得不撤退,险些未能全身而退。
咨询:关于重庆新政府,目前存在的反对势力反抗状况如何?他们实施了哪些具体的反抗措施?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镇反运动应运而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战火仍在蔓延,国民党趁机大肆渲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与此同时,那些曾经的潜伏者也开始暗中活动,他们通过电台与台湾保持联系,成立了“反共救国军”和“反共保民军”,暗中散播反动思想。在重庆,这些分子的行径愈发嚣张。在解放初期,他们便冒充解放军接管工厂。1950年初,重庆周边的璧山、铜梁两县,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当时,成千上万的匪徒围攻我们的县城,气焰嚣张至极。而璧山与重庆相距仅有几十公里。
以一典型事例为鉴。重庆的首位市长陈锡联,当时还兼任三军团司令的职务。在他乘车进城时,竟然有人向他的座驾投掷手榴弹。1949年11月下旬,少数人企图对军工厂进行破坏,意图将所有军工厂和钢铁厂一并摧毁,电厂和电台也在破坏计划之列。由于部分特务慌乱失措,这一情况被地下党组织及时发现。
成功被破坏的案例实属罕见。1949年11月29日之夜,长安机器厂内储存炸药的仓库不幸发生剧烈爆炸,邻近的刘家台居民区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即便我身处市中区,亦能感受到那股震撼人心的震动。当时,他们正身处大溪沟电厂,炸药已埋设其中。面对危机,我们的工人们临危不惧,奋不顾身,最终成功挫败了这次破坏阴谋。一些工厂主对他们表示了同情,甚至允许他们安全撤离。在我创作《绣花鞋》这部作品时,其中关于国民党企图炸毁电厂的情节,正是基于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
在开展镇反运动的过程中,有哪些具体案例发生?根据西南局的报告,1950年2月5日,发生了一起土匪反抗事件,造成179师师长朱向璃不幸牺牲。能否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一事件的经过?
这情形并非局限于重庆一地。当时,我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在边疆地区,职责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晰。凡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既无需过多探询,亦无需过多讨论,这乃是公安部的常规纪律。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由周兴担任,他此前曾任职于陕甘宁边区政治保卫局,随后被调往云南担任省委书记。副部长一职则由赵苍璧接任,他后来更是升任中央公安部长。另一位副部长刘炳琳,之后被派往山东担任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架构,便是正部长一职配以两位副部长。
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正处于巩固阶段。在此关键时期,国家制定了镇压反革命的策略。1951年3月,重庆市遵循中央的统一部署,实施了三次声势浩大的逮捕行动,这些行动均由重庆市公安局负责执行。我有幸亲身参与了其中的一次,即1951年3月13日发生的“三一三大逮捕”。
这无疑是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伟的一次行动,那一夜间便成功抓获了超过4000名嫌疑人。作为五处的一名干部,我们通常秉持着不干预当地事务的原则,仅是进行必要的了解。然而,鉴于此次行动中抓获人数众多,市公安局的人力资源显得略显紧张,不得不向西南公安部请求增援。于是,部里便紧急调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同志前来支援市局。
解放军叔叔再见
记者提问:在此次三一三大规模抓捕行动中,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安排有哪些?
就细节而言,我所能描述的仅限于我所亲眼见证之事。那时的我,年仅二十岁,还跻身于年轻干部的行列之中。三月十二日的午后,我们接到了来自上级的紧急指令,处长紧急召开会议,通知我们当晚有一项紧急任务,需我们前往支援市公安局。除我们这些干部外,还有来自边防训练班的学员,总人数约在一百到二百人之间,他们将接受市局的统一调配。
我们被安排在重庆南岸区,那里的分局局长辛嘉功,日后荣升为市检察长,正是他向我们详尽地阐述了敌情。任务一经分配,我便被派往南岸区龙门浩的下浩派出所执行任务。与我并肩前行的,是来自西南军区警卫团(当时已更名为公安团)的战友们,他们的装备精良至极,手持的都是先进的圆盘式冲锋枪。
肩负着抓捕十一名反革命分子的重任,我担任了领队。我身边有着一名户籍警和一支强化班,总兵力约在十七八人左右,每个人紧握着手中的冲锋枪。这些队员都是经验老道的战士,战斗力相当强悍。紧接着,我们获得了一份详尽的名单,上面清晰地记录了每位嫌疑人的住址,正是依据这份名单,我们开始了抓捕行动。名单是由各派出所汇总上报,经公安分局和镇反领导小组审核确认后,所有被认定为目标的名单均已得到批准。名单中对每个人的身份和背景都有详细描述,户籍警在现场负责辨认。自解放以来,即便是反革命分子,也都完成了户口登记,其中部分人则是通过细致的摸底调查而被发现。那时,我们的目标异常明确。
记者:能否请您详细描述一下那晚的逮捕行动的具体情况?
自3月13日凌晨零点开始,直至上午八时结束,这一过程在我们行业内被称作“收秤”。在这短短的11个小时里,每个人平均耗时不到一小时便完成了捕捉目标,任务的紧张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此次行动的指挥重任落在了户籍警的肩上,当时全城实行了戒严,当夜的口号便是“镇反”。若有人答不出口令,便会被视为敌人。
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目前已遭逮捕。紧接着,两名执法人员上前,迅速将其制服并为其戴上手铐。
在执行那场行动时,手铐显得格外紧缺,公安局的储备有限,因此只得临时用粗麻绳替代,迅速将众人的手绑在了一起。众人被排列得如同“珠链上的鱼”,每一条麻绳都牢牢系在他们的左臂上,依次前行。一旦有人被抓获,就必须进行常规的搜身检查。当时,几乎没有人试图反抗,若有抵抗,必须迅速将其制服;若是情况紧急,即便是动用枪支也在所不惜,幸而并未发展到那一步,因为现场的火力充足,没有人敢尝试逃逸。他们心中也都明白,为何会受到这样的抓捕。虽然没有人开口争辩,但为了避免误抓,必须确保将每个人辨认得清清楚楚。
随着第七轮或第八轮行动的推进,曙光即将破晓。本次行动的焦点锁定在了一贯道的点传师身上。门扉开启,依照惯例,我们发问:“难道你就是那个反动会道门的头目,某某吗?”户籍警核实了他的身份,他没有否认。随后,我们宣读:“你已被捕。”在搜查过程中,我手持手电筒,细致地检查着,忽然在带穿衣镜的柜子底部,发现了一双黑色鞋底,白色花纹的绣花鞋,似乎有轻微的颤动。我心中猛地一震,迅速拔出枪支,侧身冲向柜子,但里面空无一人。那双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难以忘怀。
“再见,解放军叔叔。”那些年,孩子们纷纷吟唱着“解放军慢慢走,我是你的好朋友”等动听的歌谣。至于那对双胞胎后续的境遇,我终究一无所知。
时光荏苒,我重返了那间曾居住着绣花鞋的主人——罗家巷200号的周先生的家。他因故服刑13年,却幸运地提前两年获释。当这个消息传来,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暖意。毕竟,能够改过自新,便是真正的救赎。
将罪犯带回派出所后,我们随即聚集至公安分局。在押送途中,我们乘坐轮渡。船身中央宽敞,数百人蹲坐其中。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将枪口对准他们的头部,以防止有人擅自移动,否则将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我们忧虑他们中有人企图跳船,若他们向一侧挤去,船只便有倾覆的危险。如今回想起来,仍感到一阵惊悚,若当时有人煽动,局势必会失控。而且,我们当时身穿棉袄,这无疑提高了风险系数。幸运的是,没有人擅自行动,我们最终将罪犯安全送至石坂坡,任务顺利完成,我便返回了单位。
中央定调子
询问者:当时又是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谁是反革命分子的呢?
当前,镇反行动的覆盖面极为广泛,其目标直指彻底撼动国民党政权的根基,以稳固新兴的红色政权。在军队中,连长及以上级别的干部,不论其是否真正持有反革命立场,均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与此同时,警察巡官及以上的官员,以及宪兵、特务等,无论身份地位,亦无一例外地成为打击重点。以会道门为例,一贯道的点传师以上级别的人员被视为反革命分子,而基层的坛主则不在打击名单之列,至于普通道徒更是不在考虑之中。这种界限划分清晰明确,一旦跨越这一界限,便即刻成为抓捕的对象。这一策略由中央政府制定,执行力度坚定而明确。
提问者:在重庆进行的抓捕行动中,是否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在基层公安机关执行任务时,是否已充分预见到并准备应对可能引发的激进势力蔓延的风险?
彼时,我尚且只是基层的一名小职员,对于高层决策的详细运作,我实属一无所知。
提问者询问:自1951年3月起,对恶霸分子实施惩处并协助群众宣泄不满情绪,此等措施是否有可能引发某些冤假错案?
昔日,重庆城内恶名昭彰的恶霸,非连绍华莫属。他在河坝之地欺凌船夫与纤夫,私藏枪械,行径不端,甚至欺凌良家妇女,与国民党势力亦有所勾结。这些消息,皆源自报纸报道。传闻,此人在朝天门遭到了公开的审判。记得1951年春天,曾有一场规模浩大的枪决,一次性处决了四十人。现场聚集了众多围观民众,他们纷纷站在坡上目睹了这一幕。那些反动分子跪地求饶,但子弹却从后脑射入,步枪的火力猛烈,子弹穿过头部,一声闷响,便命丧黄泉。对待罪孽深重、民怨沸腾的罪犯,便是如此严厉处置,旨在打击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然而,冤假错案在所难免。如此大规模的镇压行动,难免会有个别误捕的情况发生。在那个紧张的时刻,数千人之中错抓几人,也是在所难免的。
提问:在众多城市竞相比较杀人案发频率的当下,重庆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至于重庆的总体数据,我实不知情。对于那些我们本无必要探知的细节,不妨任其保持神秘。
提问者:请问您在亲身经历镇压反动势力行动期间,当地政府是否对此过程中出现的过度抓捕和处决情况进行了反思?
面对紧张的敌情,为确保新生红色政权的稳固,采取必要手段捕捉那些意志坚定的敌对势力分子,显得尤为迫切。若不将其绳之以法,他们必将卷土重来,届时斗争将变得更加残酷。至于宽严相济的具体分寸,还需进一步研讨。综上所述,对于镇反运动,我们不宜轻易地予以否定。
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某些时期处决速度过快。从古至今,这种做法或许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斗争取得的,若有人试图破坏这一政权,不加以镇压将如何自处?在初期,为了稳固其政权,共产党甚至觉得对敌对势力的镇压力度不够。
提问者:公众如何看待镇压反革命的行为?针对重庆地区,镇压反革命的成效如何?此行动完成后,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
彼时,民众普遍表达了坚定的支持。这份拘捕名单并非凭空而出,其中涵盖了众多来自群众的举报和秘密上报的信息。在行刑当日,人潮涌动,民众纷纷表达了对正义的拥护。众多人是有组织地前来观看,现场秩序井然,并未出现任何骚乱迹象。当恶霸连绍华被迅速处决,人群中洋溢着欢欣鼓舞的情绪。那是一个剿匪和镇反的关键时期,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遭到了重创。此举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自此之后,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生产和生活的秩序也恢复了常态。在推进镇反工作的同时,我们亦未忽视生产的发展。随着生产水平的提升,诸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提问者:您在早年时期对阶层以及阶层间的斗争有何看法?
自幼,我诞生于一个并不低微却亦非显赫的剥削阶级家庭。投身革命事业后,我对革命真理的信念坚定不移,未曾有过丝毫的动摇。起初,我对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并未有所察觉,直至反右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其激烈的程度。
优等、尚可、略有瑕疵但已修正,以及第四类——阶级敌人。我自诩对共产党忠诚至极,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却因一本尚未出版的著作,竟意外地转变为共产党的对立者。那段反思的经历让我深受触动,而在此后参与公安部门的肃反、反右和审干等任务时,我仔细查阅了大量档案,对那些往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反思。
靠谱的证券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股指配资股市有哪些翻身不仅是有钱很多人对翻身的理解是:让自己变得有钱
- 下一篇:没有了